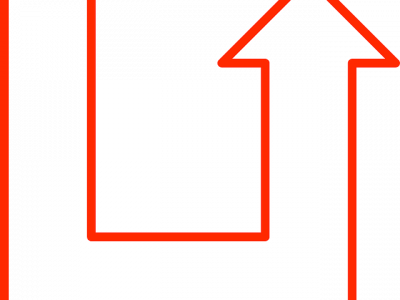当获悉我开始联络刚毕业的学弟妹时,一名小学弟自动打电话给我,在还没开口问就抢先告诉我,他已工作一段时间了。
很自然的一句话:“在那一间公司上班?”出乎意料:“我还没成立公司,目前手头上刚要完成一家公司的工作,正努力竞标另两家公司的社媒项目。”
这名时常听到我讲解零工经济的毕业生,竟然选择了我一直都认为是坏处比益处还多的自由职业者。
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份固定工作时,他的理由很简单,固定就是被“绑死”,等于没有自由。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努力也可在多间公司获得应当的回酬。
虽然很欣慰看到他带有千禧一代新企业家的风范,也了解现代年轻人“不在乎天长地久”的心态。
更理解到零工经济能为社会新鲜人带来灵活性丶独立性丶工作种类多样化丶以及不断尝试新工作的机会。对于缺乏学术文凭者来说,它更提供了入门槛较低的就业机会。
早在四年前,我国高等教育部已要各公立大学探讨Gig Economy(零工经济)这另一替代的就业机会。

当时对于这英文名词确实感到陌生,自已也作了些功课,不得不重温当年念工商管理硕士的人力资源课本。
在这过程中也让我想到1998年在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向约翰.珀塞尔教授(Professor John Purcell)请教人力资源策略的那一刻。
他当时分享了组织核心与外围(Core and Peripheral)概念在策略上为起点的重要性,而后又如何形成执行上的外包(Outsourcing)以减低组织的包袱。
处于经济革命之中,组织会把成本降得最低,无形中就会把它们转移到他处,减少固定雇员也在考量之中。
因此组织或公司的外围工作就要外包,除了尽量降低财务成本,也可免除人力资源管理上的烦恼和纠纷。
这难怪Gig Workers或Giggers在美国与大多西方国家早已风行多时,零工经济在我国处于疫情的时期也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疫情爆发前的2018年,国大学生就业事务处安排了由刚升任处长的我来主持以“解剖零工经济”为主题的讲座会。三名主讲嘉宾为高等教育部代表丶商业界代表和我的直属上司作为校方代表。
我们都认同上述的好处,但也不否认零工经济给从业者带来的坏处。个人之见,主要是在于公司转移成本计算所造成。
这些坏处是从业者获取的收入不一致,公司支出的薪水只能适中,肯定是能省就省。也因此造就缺乏福利以及潜在的压力和倦怠的工作环境。还有从业者需要承担隐形的费用和负责税务开销,完全缺乏保障。
处于校方的立场,我们有责任向学生灌输尽量避开蓝领或服务零工的性质,应以他们所学的专长从事专业性质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即使在零工经济领域也能学以致用。
在座谈会中,我们也向官方代表反映零工经济最欠缺法律保障,还有日后退休养老的安全网又如何保证不会受损,这关联到整个社会的职场生态。
政府在去年六月推出短期经济复苏计划时,初次看到零工经济社会保障计划(Program PenjanaGig)被纳入在政策里。可说是既可喜也可忧。
政府拨款数额五千万令吉可让三十万名零工经济从业者受惠,这些目标群体都属于弱势的蓝领零工阶级。
在推行该政策时,也有评论担忧将助长各行业倾向于通过零工经济这非正规就业方式,来避开支付社会保障费用。
每项策略的执行,有利也有弊。零工经济这非传统雇主与雇员关系性质的工作也无可避免。
在此呼吁社会新鲜人,尤其是零工经济从业者,更要深思。除了自力更生,更要懂得维持理财的自律人生。

张炳祺博士〈公关小贴士〉专栏